[东方早报]“汉学家也有自己的‘中国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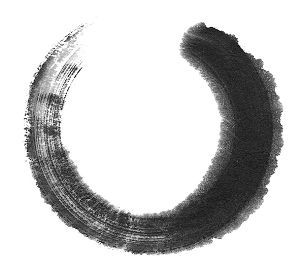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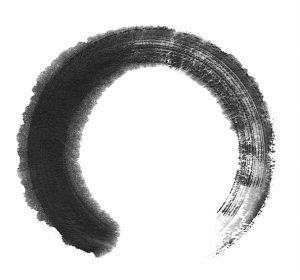

傅高义说,汉学家们也有自己的“中国梦”:“让中国学者发挥自己的作用,和外国学者交流;让我们看到尽可能多的材料,与中国学者交换看法,提高对中国的理解。”
早报记者许荻晔发自北京
9月6日,由国家汉办(全称“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与中国人民大学共同主办的第四届汉学大会开幕,来自38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名专家学者将在两天时间里聚集人大,从多学科视角就东西文化交流展开对话。
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原主任、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傅高义,法国巴黎索邦大学校长巴泰雷米·若贝尔,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汉学家协会主席弗拉基米尔·米亚斯尼科夫,原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校长阿冯斯·腊碧士,国际哲学协会联合会主席德莫特·莫兰,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主席汉斯·伯滕斯等均出席了大会。
汉学即中国学,指中国以外的学者研究中国的学科,研究方向可包括中国历史、政治、社会、文学、哲学、音韵学、史学、经济、书法等,甚至也包括对于海外华人的研究。从1814年12月11日法国汉学家雷慕沙在法兰西学院主持第一个汉学讲座算起,学院式、专业化的中国研究至今已存在了200年。
2007年,中国国家汉办与中国人民大学发起举办第一届世界汉学大会,以“文明对话与和谐世界”为主题,而后在2009年、2012年,分别又举行了“汉学与跨文化交流”、“汉学与当今世界”为主题的两届大会。大会以“东学西学·四百年”为主题,设有诸多议题:《元典互释与东西文明:思想对话的“中国主题”》;《文化沟通与双向影响:历史钩沉的“中国记忆”》;《文化塑成与经典翻译:域外变迁的“中国形象”》;《文化传统与制度选择:当今世界的“中国角色”》等。傅高义、杜维明、艾恺等知名汉学家在这两日内均有主题发言。
傅高义在开幕式上介绍,汉学家在研究中国的过程中,遇到的比较大的问题一是自由,二是媒体声音,但他认为“给外国人机会来到中国是好的,我们早晚水平会提高的,可能暂时会有一些困难,但是长期是好的”。傅高义介绍,汉学家们也有自己的“中国梦”:“让中国学者发挥自己的作用,和外国学者交流;让我们看到尽可能多的材料,与中国学者交换看法,提高对中国的理解。”
被掩盖的比丘林
汉学产生的一个重要源头是来华传教士。早在路易十四时期,法国科学院便派传教士前往中国。早期的“汉学”主要处于典籍翻译阶段,也渐渐将一些中国文学作品带入欧洲。如伏尔泰当年在法国颇为轰动的戏剧《中国孤儿》,即根据传教士马若瑟所节译的纪君祥《赵氏孤儿》改编。除了翻译,早期传教士们的中国论述也在欧洲流传、出版,但观点总体而言流于表面、片面,甚至不乏歪曲。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汉学家协会主席弗拉基米尔·米亚斯尼科夫认为,汉学从典籍翻译转变为一门有科学方法的学科,俄罗斯传教士比丘林功不可没。比丘林1807年来到中国是为了传播东正教,但这样一个业余汉学家,在中国待了40年,走遍中国大地,乃至满洲、西藏、蒙古等地区等都留下过他的足迹,涉及中国的历史、地理、经济和文化。其人离开中国时,带走的手稿、图籍达1.4万磅,分装15头骆驼驮运,米亚斯尼科夫认为,“比丘林是俄罗斯东方研究经典学派的创始人,他也非常成功地将俄罗斯的人文研究与欧洲的汉学相结合,建立起了汉学研究这个学科。”
米亚斯尼科夫将这位东正教传教士与著名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对比:两人同年来到中国,都有很高的中文水平,都编写了中文词典、语法书,但命运截然不同。1824年马礼逊回到英国,受到国王接见,在伦敦的精英圈子很受欢迎,并引领起英国人对中国的兴趣;而1822年回到圣彼得堡的比丘林直接被流放了4年。结束流放后,比丘林邀请普希金一起去中国却遭到拒绝。
米亚斯尼科夫介绍,马礼逊与比丘林对中国的著述里,不仅有关于中国的统计学描述,也着重在语言、历史、地理、政治、宗教、风俗、民情等角度深入理解这个古老帝国。“比丘林希望能够真正提供一个关于中国的论述,他关于中国的知识使他很受理藩院的欢迎,因为他可以翻译来自欧洲国家的信件。他对语言的掌握也使他能够和中国各个阶层的人打交道并收集各个领域的信息。”
大量的信息使比丘林改变了最初介绍中文语法的计划,1828年到1830年,他出版介绍了西藏、蒙古等历史与现状的书籍,翻译了中俄对照的《三字经》,还写了一本书关于成吉思汗家族的四大可汗,在其《北京志》里,还绘制了1817年的《北京城郭图》。“1848年,比丘林出版《中国的行政和风俗概况》是一部百科全书似的著作,分为四个部分介绍中国,他的一些观察和结论成为后来研究中国人的民族志心理学的科学基础。”
二战后的汉学
二战以后,海外汉学的研究重点转向现代中国。巴黎索邦大学校长巴泰雷米·若贝尔回忆,1973年,中国在巴黎举行了出土文物展览,这是新中国的出土文物第一次在国外展出,但集中了从60万年前的蓝田人时期到14世纪元代的艺术珍品。若贝尔当时还是一个小男孩,但他记得他的家人与公众都非常兴奋:“通常来说他们对于中国的东西没那么感兴趣,但法国公众第一次能看到中国的艺术品,其中甚至包括在中国刚刚被挖掘出来的青铜器。这是东西方文明分离几十年后第一次再见面,也是我们卓有成效的交流的开始。”
到1993年,若贝尔在板球队的一个朋友娶了一个中国女孩,整个板球队将新娘轮流扛在肩上,扛到了新郎家,因为他们以为这是中国的结婚传统,“虽然我不知道是不是严格按照中国的方式来做的”。今年中法建交50周年,最令他感慨的是,“从国家的关系恢复,到艺术的交流,再到人与人的交流,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当中我们两国走过了多么长的旅程啊。”
费正清东亚中心第二任主任傅高义则认为,二战对于美国,可能也有中国改革开放般的意义:二战之后,美国开始意识到了解世界的重要性。费正清在美国汉学研究中功不可没,不仅在于其学术成果,更在于推广了这个学科:“费正清那一代的梦是培养中国学学者,让政治系和法律系有专门研究中国的人。当时社会学研究中国的没有,虽然我很年轻,但费正清先生培养我作为一个社会学系的中国学学者。当时虽然美国没有办法跟中国交流,但我们相信慢慢是有机会的。”
2000年从哈佛退休后,傅高义开始研究邓小平,“我思考我该做什么,来帮助人们理解一些其他国家正在发生的变化,所以我主要关注的是让人们理解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而写出《邓小平时代》,他最感谢中国的学者和官员的支持。相比“改革开放的建设者”,傅高义更认为邓小平属于“总设计师”,他认为邓的做法更近于实验:“我觉得他没有清晰的蓝图,虽然他已经决定把市场放开一点试试看。但他没有用西方或者苏联的方法来实验,他用适合中国的方法来实验,并根据实验效果继续工作。”
“我认为中国是非常幸运的,在改革开放中有邓小平这样一个领导人。”傅高义说。他认为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需要双方极大的勇气。1978年5月,卡特派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秘密转达了建交意愿,当年夏天开始谈判。中美正式于1979年1月1日建交后,邓小平在1月底访问美国。在得克萨斯时,一名牛仔送了一顶牛仔帽给邓小平,他笑着戴在了头上。
“这张图片出现在时代周刊封面上,成为新中国的一个象征。而对于中国国内,很多人那时觉得美国是帝国主义,但看到邓小平作为国家领导人在美国的表现,感觉很好,这时候人们开始研究美国。”傅高义说。
从世俗人文主义到精神人文主义
在米亚斯尼科夫看来,相对西方汉学以旁观者角度来分析中国现实,中国的汉学“分析的是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这种中国汉学有着一些基本理念,比如中国的和平崛起,就是给中国文化一个关键的作用,以此去建立和平、和谐的世界文明”。
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昨日提出,基于儒家传统的精神人文主义是汉学研究当中非常重要的领域:“表面上它似乎不会影响中国和平崛起的前景,或者是去影响第一世界的国家来接受中国成为一个多极化世界中一个重要的角色的过程,但是从整个世界观念的角度来看,如何找到一个和平发展的可持续方法,以及文化上能够对话与理解的方法,这需要我们新的思维方式、新的伦理以及新的宇宙观。”
德国思想家马克思·韦伯曾有论断,世俗人文主义已经成为主要的意识形态,乃至很多方面已经超过了宗教。杜维明认为,世俗人文主义最明显的表征即是民族主义。而一个世纪以来,关于中国的论述,又被科学物质主义与工具理性主义所主导,他认为中国的道德危机主要是信仰缺失,尤其年轻人缺少敬畏感。在这种情况下,强调天人合一、天下和平的精神人文主义,推动的是对话、和解与和谐,“和谐的前提是不同,可以有不同价值的观点比如理性主义、环保主义、多文化主义、宗教多元主义等观点共同地形成合力,成为普遍自觉,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永久和平的愿景的基础。”
杜维明强调,要达成精神人文主义,人不仅要进行自我的修身,也要建立人类的共同体,并且尊重自然,除此之外,他提出第四个维度:尊重天道。他介绍,在他的“跨宗教和跨文明的对话”中,发现儒学是可以超越汉语文化圈、中华文化圈,走向全球主义的。“自2013年以来,中国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GDP对于发展只是一个非常有限的衡量方式。除了经济的因素,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的维度必须被包括在全面发展战略之中,这样一个更加广大的愿景,让我们非常有勇气、有创造性地去思考中国可以传递什么样的文化信息,它会是多元的、开放性的,而且是自我反思的。中国不能成为一个民族主义国家,而应该实现它的文化理想,成为一个跨国家的、精神性的文明主义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