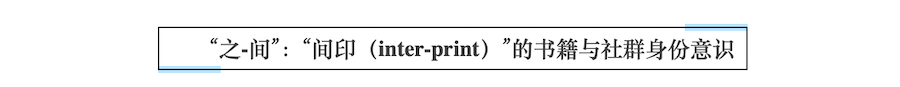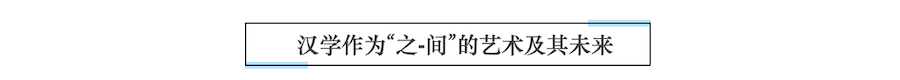人物专访
【汉学大会·访谈】钟鸣旦 | 在历史“之-间”的相遇:十七世纪中西书籍交流与文本社群的建立
2018-11-06

钟鸣旦教授,荷兰莱顿大学汉学博士,比利时鲁汶大学(荷语)汉学教授,比利时皇家科学院院士。长期致力于欧洲汉学研究,尤其是十七世纪中欧间的文化交流研究。主要著作:《杨廷筠——明末天主教儒者》《本地化:谈福音与文化》《可亲的天主:清初基督徒论“帝”谈“天”》《传教中的“他者”:来自中国的教训》《礼仪的交织:明末清初中欧文化交流中的丧葬礼》等。
钟鸣旦教授的研究集中于书籍在中西文化“之-间(In-Betweenness)”的巡回,并试图勾勒这些书籍如何在17世纪的中国构建了以“之间人”为主体的文本社群。钟鸣旦教授谦逊地说,这是一个宏大的研究项目,我将要谈论的与其说是一些研究结果,不如说是我的部分研究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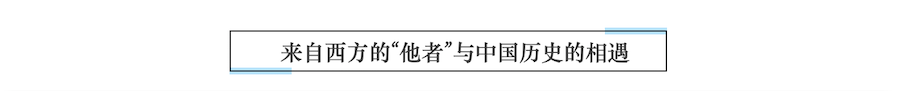
钟鸣旦教授师承荷兰著名汉学家许理和教授,受到汉学、宗教学和人类学的学术训练。他自步入汉学研究领域便始终关注着这样一个问题:当两个文化或文明相遇的时候,会发生什么?钟鸣旦教授说道,历史研究可视为关于“他者”的艺术,因为历史学家考察的是生活在另一个时空的人。“他者”同样也处于文化交流史研究的中心位置,因为历史学家往往通过与“他者”文化的相遇去理解所发生的事情。
那么,当我们以历史学的眼光去研究与“他者”的相遇时,我们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论呢?钟鸣旦教授给出的答案是:他者性的理论(theory of alterity)。他者性理论有很深的哲学根源,如布伯(Martin Buber)、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和利科(Paul Ricoeur)等哲学家都有过相关论述。他们给钟鸣旦教授研究方法论上的启发是:文化之所以成为如其所是的文化,是通过与他者的相遇以及随之发生的沟通而是的;没有他者文化的观照,就没有文化的自我;文化永远处在与他者的联结关系之中;处于文化中的人的身份并非是固定不变的,通过与他者的相遇,身份可以被构建和塑造。
因而,钟鸣旦教授在处理17世纪中欧之间的相遇时,会格外注意传播、接受、创新和交流间的多重互动。两个文化间的相遇应该被建立在这样一种多重互动框架之中,才能彼此互为视点,从不同的视角审视历史,以期望更好地与“他者”文化进行对话。首先,在传播视域中,传播与交流是同时的,因为人们在传播信息的同时,又渴望能够被他人理解。其次,就接受视域而言,接受同传播一样,都是一种双向行为,处于交流中的接受者,在接受信息的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信息。因此,在这一多重互动的框架中,无论是作为天主教的接受者中国,还是作为传播者的西方,都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前提:任何相遇与交流都会不可避免地遭遇“误解”与“不可理解”。这一多重互动框架提供了多元的理解视域,为创新留出了生成与转化的空间,创新就是文化与历史“之-间”的对话与故事。
钟鸣旦教授认为,17世纪中西交往的历史背景与时代特点赋予了基于书籍的巡回传播的文化研究以可能。一是,中欧两种文化在文化传承方式上很相似,这里主要是指印刷技术——中国木板印刷技术简便,欧洲人不需要引进印刷机或开设印刷作坊,便可以制造大量的书籍,而低廉的价格也有助于促进书籍的广泛流通。二是,中国当时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机构组织进行系统的出版审查,也没有如教会这样的组织监管出版物中的异端思想,因此,传教士和天主教徒们可以自由地刊行他们的思想。三是,“刊书传教(Apostolat der Presse)”是当时传播福音的主要方式。天主教的传教活动与书籍的文化巡回,打开了文化与历史“之-间”的意义生成空间。
“之-间”是所有一切的关键,那么什么是“之-间”呢?钟鸣旦教授受到日本学者和辻哲郎对“间”概念的阐释(“间”包含四维:空间、时间、世间和人间),以及香港学者梁元生在《边缘与之间》论述的“之间人(in-between person)”的影响,他把来自东方的解释与西方哲学的“间隔”概念相结合,认为文化的“之-间”有四层意思:一是将两种文化区分开来的界限或间隔;二是两种文化之间的空白位置与空间;三是限于两种文化或多文化间的共同行为,如:“中欧之间的交往”;四是表示两种文化间的视角选择。这些不同的含义也出现在以“inter”为词根的一些词里:间隔(interval)、空隙(interstice)、互动(interaction)、干预(intervene)、中介(intermediary)、对话者(interlocutor),等等。
然而,“之-间”的魅力并不仅仅在于这个概念的内涵与其背后的思想性,更在于“之-间”本身具有的力量与孕育力。钟鸣旦教授借助“间(inter)”与“印刷(print)”发明了一个新的概念:英文inter-print,对应的中文是“间印”和“间刻”。狭义的“间印”或“间刻”是指:一个文本中既有中文,又有西文,且中文和西文部分并不是处于互为翻译的关系之中,而是共建了同一文本的现象。广义的“间印”可能还包括,将西方书籍的制作和设计方式移置到中文的书籍之中,如:中文书籍中插入了索引部分,或者是对西方传教书籍中的人物插画进行改造,将其中朝拜上帝的西方人换成中国人的形象,以及大段引用西文传教译介作品并加上接受者的解读而写成的另一本书,等等。
那么,这个以“间印”书籍为纽带,基于中西文化“之-间”的文本社群是怎样的一个形态呢?钟鸣旦教授分别从生产制作、分布流通和阅读消费三个环节对文本社群进行考察。在书籍文本的生产制作环节,我们可以从一些书的封底或扉页,看见“某某人准,某某人校,某某人印”的字样,或者标有:政府(官刻)、商业作坊(坊刻)、私家(家刻)、寺廟道观(寺观刻)、教会(堂刻)的名字。在分布流通环节,主要涉及到对两个方向的考察:其一是在书籍的内部文化传播,如:这些书籍影响了哪些宗教社团?这是面向教会内部的还是外部的?其二是针对书籍跨文化间的传播,如:中文书籍如何流传到欧洲并分散到各地?它是怎么发生的?最后是阅读消费环节,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在当时中国的天主教徒中,有九成是文盲,只能聆听他人布道,只剩下一成的人群能够阅读这些书籍,他们是这一环节考察的主体。钟鸣旦教授通过对私家藏书的搜寻和研究以试图定位他们的身份。
当我们谈论文本社群的时候,会涉及到对这些“之间人”的身份界定问题,而身份又是与认同息息相关。“间印”书籍与“之-间”社群形成的关系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考察因为书籍的交流而形成一个文本社群?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真正指涉的是:透过文化“之-间”的书籍文本去发掘其背后的身份认同问题。这又可以被分解为诸多具体的方面:一种文化或多元文化的意识是如何贯穿于文本中的,信息是如何被安放于具体书籍文本的社会历史语境之中的?在文化“之-间”的书籍社会史中,在印刷物和印刷的社会化过程之间的双向互动中,文本对塑造的身份意识发挥着怎样的作用?这些问题意识具有现实的关切:一个有意识的文化输出如何通过文本的印刷出版去引发“他者”文化的接受和认同。
钟鸣旦教授认为,汉学是一门处理“之-间”的艺术。汉学的“之-间”是对存在身份的一种追问,是一种思考方式,也是一个关于注意力的问题。
汉学家身份的特点与许多人类学家相似,他们始终在文化之间旅行,周转,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在他者文化(汉文化)中小憩一会,然后又回到母文化之中。乍看起来,这似乎要求汉学家在两种或多种文化中做出选择,但事实上,他永远不能完全回到或进入任何一种文化之中。汉学家是一群“之间人”,在“之-间”不仅是外部的表现,而且就是汉学家本人。这一身份的过程要求他们学会遗忘和淡化自己的身份,以获得“汉学家”的身份。这一身份又是积极的,获得身份的过程需要感同身受,因此,汉学家在与中国产生个人与普遍的联系之中成为了一个“故事”,一个试图去达成理解的“故事”。
汉学通过“思考之间”与“焦虑界限之间”去重新思考概念及其之间的边界。汉学在本地,即汉学家的所在地,总是无以为家;因为汉学总是让步于那些强调永恒价值与质疑反思的主流理论和价值实践研究。汉学家,如同任何一个区域研究专家,始终在面对“陌生感”,做“他者性”的研究。“他者”之所以引人入胜,在于它总是在逃逸,无法被真正把握,因而,汉学家总是在“理解”与“误解”之间生产出新的意义价值。
汉学“之-间”关涉注意力问题,既专注于“之-间”,又受其干扰。注意力在于“间隔”,无论做哪方面的研究,汉学家都应该自问:研究的“之-间”在何处?注意力也在于边缘,例如发掘中文文献书页边缘的附加信息,汉学研究的意义恰恰在于给边缘以话语权。关注“之-间”是将注意力引向另一个空间:非二元对立,非此即彼,而是寻找发生在双方之间的“互动”,关注各种形式的相遇和对话,这也是对于关注复数形式汉学(Sinologies)的有力回应。
钟鸣旦教授谈到,虽然汉学研究相对于西方主流学术界而言,依然处在边缘的位置。但随着中国的发展,西方必然会将越来越多的目光投向中国。也许他们不一定是真正对汉学感兴趣,但是西方对于中国一定会抱有很大的兴趣和热情。也许西方社会目前还不能完全地理解中国,但是“完美地理解”本身就是一个悖论,随着中西之间学术交流的加深,双方互派留学生的潮流愈发盛行,相信西方世界以及学术界未来一定会更加关注中国,理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