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内容
【汉学大会·分组会议】第一分组:“汉学的译介与对话”
2018-11-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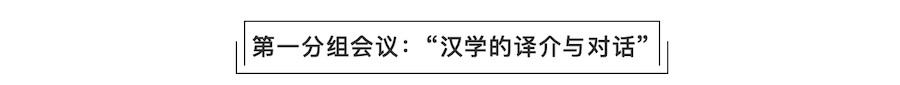
2018年11月3日下午,第六届世界汉学大会的分组会议“汉学的译介与对话”第一、二场会议在国学馆123举办。著名汉学家罗伯特·恰德、安乐哲、李夏德、费南山、张华分别就相关汉学议题作了主题发言。 2018年11月4日上午,第一分组会议“汉学的译介与对话”第三、四场在国学馆123会议室举行。耶鲁大学司马懿教授、圣彼得堡大学罗流沙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马小红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麦克雷教授和蒙古国立大学巴特玛教授针对相关议题先后作了主题发言。
第一场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诸葛忆兵教授主持。首先,牛津大学罗伯特·恰德作了题为《前现代汉学研究步入近代》的发言。罗伯特·恰德教授主要介绍了西方汉学的起源,并结合自己的教学经历介绍了牛津大学古汉语发展的情况,以及西方汉学对于学习古汉语的作用。到牛津大学任教以后,罗伯特教授学习了约翰·奇科斯基的教学原则,在每一课都布置语法和短句的练习。由于缺乏上下文,所以对学生对语法的掌握要求非常高,而罗伯特教授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培养学生的语法能力。很多学生经过三个学期的学习之后,汉语水平得到了惊人的提升。他认为,学习汉语,尤其是古代汉语,有数学、古典学、希腊语学习背景的人往往学得最好。


紧接着,第二位发言人、北京大学安乐哲教授作了题为《将中国哲学译入西方学界:迟做总比不做好》的报告。通过引用葛瑞汉、尼采、亚里士多德等学者的观点及其中外翻译的对比,安乐哲教授介绍了中西方学者在世界观和宇宙论方面的不同点。 他认为,亚里士多德从本体论出发,以对名词的探讨为核心开始对世界的思考;葛瑞汉则认为事物出现的时候并不是独立的,而是彼此联系、彼此依赖的,并没有某一种事物针对其他事物的优先性的;相比之下,中国的宇宙论传统则聚焦于“什么是人”和“人从哪儿来”的问题,把人、事物和地点连在一起,这与以动词为中心的中国语言是非常不对称的。

维也纳大学李夏德教授作为第三位发言人,以《太平御览》为主题,介绍了奥地利汉学家奥普菲茨梅尔把《太平御览》翻译成德语的情况,并作了《宋代类书<太平御览>:菲茨梅尔德语译本的选译性与学术性》的主题发言。李夏德教授简要介绍了奥普菲茨梅尔的生平,并着重介绍了奥普菲茨梅尔对汉学的贡献。在获得了维也纳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的博士学位后,奥普菲茨梅尔翻译了白居易的诗和《汉书》,并留下了大量《太平御览》的译本。庞大的译文为那些不懂中文的人提供了一个机会。李夏德教授向大家展现了一位热爱中国文化并致力于传播中国文化的奥地利学者。

短暂的茶歇后,中国人民大学杨慧林教授主持了第二场会议。首先爱丁堡大学费南山教授作了《更新转化的术语:论当下晚清翻译研究的重要性》的报告。费南山教授介绍了三位晚清的翻译家,并谈了文本对于知识传播的影响,最后着重探讨了翻译对于言论自由文本的影响以及对当今时代的意义。她指出,早期人们对于翻译传播和著作的概念没有明确区分,但17世纪之后,德国和荷兰出现了新闻自由,人们可以畅所欲言。19世纪,当地有著作专门介绍当时的中国,用到了很多词语,包括晚清出现的术语也会在报纸、刊物和百科全书里出现。因此,我们必须要对翻译文本本身的集聚价值给予应有的重视。


最后,北京语言大学张华教授结合亲身经历,介绍了他对“国学”“汉学”等词语在翻译问题上的观点和坚持,并做了《国学与汉学》的发言。早年人们用英文“National Studies”一词指称“国学”,张华教授认为这一译法颇有“硬译”之嫌,曾提出应把“国学”对译成“Classics”的看法,却应者了了。2018年,在他主编的《东学西传:国学与汉学》出版前,“Sinology”指称“汉学”已是共识,但对于“国学”一词,张华教授下意识地给出了“Classics”的翻译。这一观点得到了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伦·米勒教授的认可,不但一目了然,而且非常有助于国际视野下重建中国古典学——即国学。张华教授认为,这其实是对西方话语中心意涵的古典学理解的放弃,因为这把中国国学也视作“Classics”的一种。

学术本无国界,对于汉学的译介与对话,本身也有很大的讨论和发展空间。在三个小时的会议中,五位学者带来了颇丰的学术果实,围绕汉学与在场嘉宾展开热烈讨论,话题涉猎翻译、教育、哲学等领域。
2018年11月4日上午,第六届世界汉学大会第一分组会议“汉学的译介与对话”第三、四场在国学馆123会议室举行。耶鲁大学司马懿教授、圣彼得堡大学罗流沙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马小红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麦克雷教授和蒙古国立大学巴特玛教授针对相关议题先后作了主题发言。
第三场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杨联芬教授主持。第一位发言人司马懿教授作了题为《重思晚清民国时期的基督教文学》的报告。过去一般认为,晚清和五四的“基督教文学”之间是分离的,司马懿教授则建议思考两者的连续性。晚清关于《圣经》和基督教教义的出版物一般被视为客观的“直译”,但实际上晚清中国译者有很大选择空间。司马懿教授通过细读威廉·曼德赫斯特的《圣经史记》以及约翰·韦恩·考特曼德的《圣经图记》,指出晚清译本并非客观,这和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从时间线、文学性、生存观等角度选择性解释基督教文本具有相似性。知识分子神学训练的缺乏、留学的经历和个体的信仰变化等,都会影响他们对基督教文本的解读。总之,晚清的基督教写作并未消失,而是持续影响五四时期的作家,晚清作家实际上重新书写了《圣经》。基于此,司马懿认为,有必要重新思考晚清和五四基督教文学的边界。


之后,罗流沙教授作了题为《论俄罗斯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的去学术化》的报告。他认为现当代文学的译介出现了显著变化,而占比更大的古典文学多为再版,变化相对较少。他梳理了1992年至今,中国现当代小说在俄罗斯的译介的三个阶段。首先,从1992年到2001年,翻译人才少质量却较高,报酬低且翻译量小。在译作的选择上,最为常见的是翻译与研究方向相一致的领域。老舍的翻译最多,司格林等大学教授是翻译主力。其次,从2002年到2009年,翻译人数增加了,质量不稳定而报酬合理,翻译量虽然增加但依然不足。虽然这一时段的中国文学译者所获报酬较高,但因文学翻译项目少,并没有专职的中国文学译者。最后,2010年以来,翻译队伍不仅增大,而且趋于多样化和职业化;虽然翻译项目大量增加,但因新手多,翻译质量并不稳定。2014年以来,中国政府开始支持这些翻译工作,译者们的工作情况大为改观。

第三位发言人马小红教授作了《礼、法字义的古今演变》的主题发言。康有为曾将中国“法”和西方“法”比较,批评中国“法”的不足;而严复主张西方“法”应该对应礼和刑,孰是孰非?为此,马小红教授引经据典,考证了礼、法两字在古代与近代的演变。“法”经春秋战国演化为中性的制度,而“礼”实为古代的“良法”。法家商鞅变“法”为军事化的“律”,为帝王所用。引进西方的“法”字后,现代的“法”与“律”重叠,实际与民主精神背离,也使得古代真正的法——“礼”的内容萎缩。现代的“礼”“法”成对立局面,实与翻译的干扰有关,因此,严复的说法更为准确。杨联芬教授进一步指出,中国人所秉持的“礼”比西方的“法”更强调实践性。

第四场会议的主持人为中国人民大学雷立柏教授。第四位演讲者麦克雷教授的发言主题是《中国的灵魂还是中国的钱?——为什么17世纪的传教士汉学家让欧洲爱上中国(兼论21世纪可能的缺失)》。麦克雷教授重点关注了17世纪传教士翻译的拉丁语汉学。他强调不管那些传教士的翻译方法如何,翻译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判断,他们只会翻译他们认为有益于西方的内容。他展示了大量拉丁语资料,并介绍其中描述中国时经常出现的主题。首先是语言和写作——传教士试图用拉丁语教中文语音、语法甚至研究中文速成法,这说明他们着迷于中文语言本身的魅力及背后的宗教思想。其次是哲学和历史——传教士翻译了孔孟论争的文献和部分中国历史,体现了他们重视中国思想的借鉴价值。最后,传教士翻译了很多地理与社会的内容,涉及地图的描述、植物学与医学、科学与技术、社会组织的管理等具体方面。


最后,巴特玛教授作了《汉蒙翻译是蒙古国中国学的关键部分》的主题报告。她梳理了中蒙翻译的不同阶段:远古鲜卑《孝经》的翻译可以视为蒙古语翻译的开端;蒙古帝国时期翻译流传下来的作品是目前研究的主体,此时四书五经已被翻译并在学校中教授。大元王朝时期,《资治通鉴》等译作在蒙古翻译史上有重要地位,而且这时的蒙汉对照字典对后世具有重要价值。明朝时期,翻译作品相对减少,这与国内政局不稳定有关。满洲时期,不允许蒙古人学习汉语写作,所以推行从满语间接翻译的政策。此时,《辽史》《金史》《元史》《论语》《孟子》《三字经》等著作被翻译成蒙古语,这些译作被视为学习中国的重要文本。在蒙古博克多汗国时期,以及后来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开始建立之时,大量中国经典作品如四大名著以及《诗经》《聊斋志异》《金瓶梅》等都得到了翻译。如今,蒙古国涌现了大批中国学研究者和汉语翻译者,他们翻译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很多作品,同时中国古代文献及史书的翻译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巴特玛教授指出,丰富的翻译传统为中蒙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